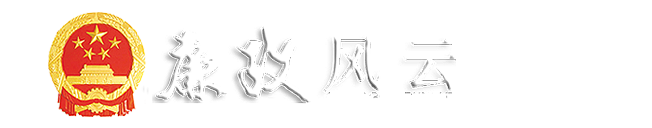在司法实践中,“执行难”已成为长期困扰法治建设的顽疾。胜诉当事人捧着生效判决却难以兑现权益,被执行人通过各种手段转移财产规避执行,形成了“转移易、追回难”的恶性循环。这一现象的核心矛盾,在于财产转移的极低门槛与司法机关追查财产的高昂成本之间的失衡。
一、财产转移的“花式操作”与低成本特性
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手段层出不穷,且成本极低。在民事诉讼阶段,部分被执行人提前将房产、车辆登记在亲属名下,或通过“假离婚”协议将共同财产划归配偶;企业主则利用财务造假、多头开户、虚设交易等方式隐匿资产。更有甚者,通过“蚂蚁搬家”式小额转账、虚构债务、虚假投资亏损等手段,将财产转移得不留痕迹。例如,某混凝土公司在执行中发现被执行人开设210多个银行账户,试图以“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名义隐匿资金,最终通过5天昼夜追踪才锁定真实财产线索。
跨境资产转移更成为规避执行的“捷径”。部分企业主通过移民将资产转移至境外,或利用国际贸易中的“低报出口”“内保外贷”等监管漏洞,将资金洗白为合法收入。这种操作不仅涉及复杂的法律灰色地带,且跨境追赃需依赖国际司法协作,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
二、财产追回的“三重困境”
1. 查控体系的滞后性
目前,法院主要依赖银行、房管等部门的协助查控,但部分机构消极配合甚至通风报信。例如,某银行以“需行长签字”为由拖延冻结账户,导致260万元资金险些流失。此外,新型财产形式如虚拟货币、代持股权等,缺乏统一登记制度,进一步加大了查控难度。
2. 法律追责的绵软性
尽管《刑法》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实践中适用率极低。2018年最高法报告显示,全国因拒执罪被判刑的案件不足执行案件总量的1%。被执行人普遍存在“拘留15天了事”的侥幸心理,而律师教唆规避执行、协助单位提供“绿色通道”等行为,更助长了转移财产的气焰。
3. 制度保障的缺位性
我国尚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对“执行不能”案件缺乏合法退出机制。同时,执行救助基金覆盖面有限,难以解决特困申请人的燃眉之急。此外,财产评估、拍卖程序繁琐低效,导致查封财产长期无法变现,进一步加剧了执行周期的延长。
三、破解困局的路径探索
1. 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
从立案阶段即推行“执行窗口前移”,强化诉前保全与诉讼保全,防止财产转移。例如,广东四会法院通过快速响应机制,在260万元资金解冻前48小时内完成现场扣划,避免了企业重大损失。同时,建立跨部门征信网络,将房产、车辆、金融资产等信息实时共享,压缩财产隐匿空间。
2. 强化法律威慑与信用惩戒
对恶意转移财产行为,加大刑事追责力度,明确拒执罪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例如,新疆高院明确,即使财产登记在配偶名下,若属夫妻共同财产或存在恶意转移,法院可依法执行。此外,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融资贷款、担任高管等,迫使其主动履行义务。
3. 技术赋能与社会协同
借助大数据分析、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手段,追踪资金流向与财产变动。例如,抖音视频中提及的“调查令+律师协作”模式,通过专业团队挖掘财产线索,提升执行效率。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推行执行悬赏制度,发动群众举报隐匿财产行为。
结语
执行难的本质,是社会信用体系与法治建设的深层矛盾。唯有通过制度完善、技术升级与社会共治,方能打破“转移易、追回难”的恶性循环。当财产转移的成本高于履行义务的代价,当失信者寸步难行、守信者畅行无阻,司法权威与社会公平才能真正落地生根。这不仅需要司法机关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全社会对法治精神的信仰与践行。
【责任编辑:于武栋】